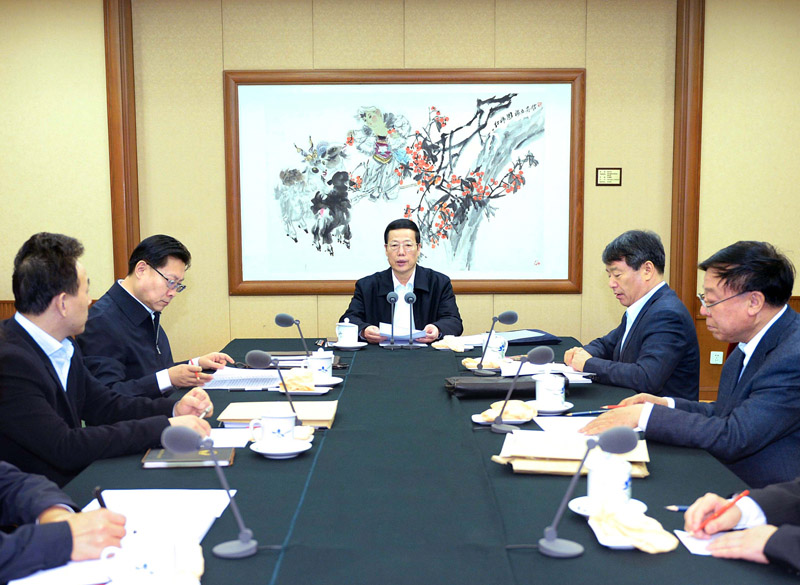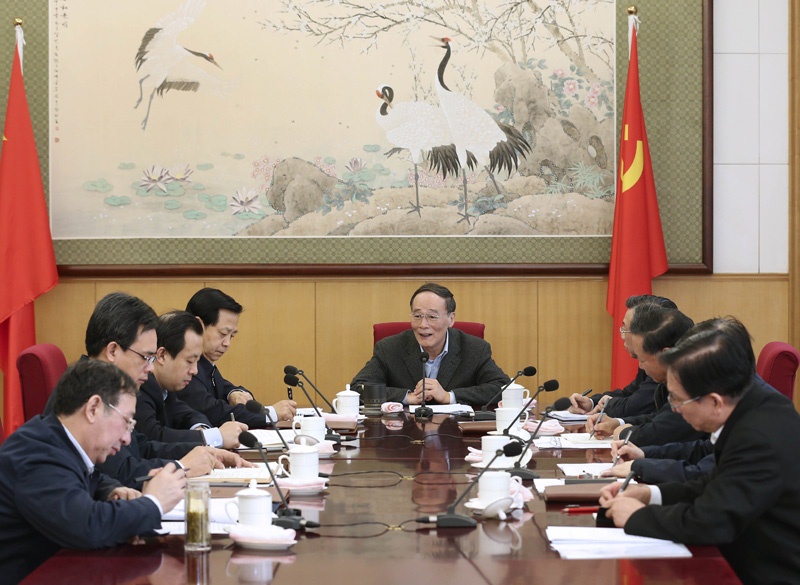群众路线网 >> 实干风采
章展:我只是一个普通人
2014年06月04日 09:50 来源: 今日黄岩
——记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章展

4月30日上午10点许,记者来到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,只见章展和同事们一起,各自对着一台电脑,正在做病程记录,记录病人的诊断情况、诊断依据、病情变化、医嘱更改以及原因分析等,非常忙碌。当他抽出时间接受我们采访时,他说道:“我其实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,我做的事也只是一件普通的事,只是我比较幸运,我的造血干细胞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配型成功。”
我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我比较幸运
今年3月4日上午9点,浙江省中医院12楼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,章展静静地躺在病床上,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。血液从他左臂输出,经造血干细胞分离器后,又输回他的体内。正是这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,拯救了北京一名“90后”白血病患者的生命。而章展也成为浙江第1例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血液科医生。
2011年6月14日“国际献血者日”,红十字会在台一医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宣传,就在这一天,章展将自己的血液资料挂在中华骨髓库的资料库里。章展告诉记者,“我们血液科四五个医生是一起去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活动,并一起将自己的血液资料挂在中华骨髓库的资料库里。只是我比较幸运能这么快匹配上。”
其实,2012年10月,章展曾经有一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机会,初配本来通过了,可惜没有通过高配。
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只是做我分内的事
在病房,我们看到有一个脑瘫的老人,不能说话,家里人忙,只有保姆照顾着。“章医生人很好,很有耐心。这个老人家虽然不会说话,但是章医生每次过来都会和她说说话,还会向我询问一些情况。我只是他们家的保姆,照顾这个老人家还是会有点担心没照顾周全,有时候一发现情况不好了,我就马上告诉章医生,他会立马赶过来。有时候次数多得我都不好意思了,章医生却一点都不嫌烦。”照顾老人的余女士告诉记者。
章展是医院内的一名普通医生,每天和同组的三位同事一起,共同完成医院里的任务。他们早上七点半来到自己的科室,在半个小时内完成交接工作。八点钟准时开始查房。十点钟左右开始处理医嘱,做好病程记录,并帮助病人办理出、入院手续等琐碎的事情。转眼间,七个年头,两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,就过去了。
作为医生,章展经常要面对生离死别。他曾接触过一个刚出生十几天的小男孩。当时,这名小婴儿躺在新生儿抢救室,小小的身子上插满了各种管子。因为孩子太小,再加上感染肺炎,医生们根本无从下手,只能放弃治疗,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新的生命陨落。那时候他的儿子也刚出生没多久,他看着这个小孩子,想到了自己的儿子,心酸、痛心、同情,五味交杂。
几年前章展还接触过一名40多岁的男性白血病患者。这名患者是家里的“脊梁骨”,上有70多岁的父亲需要照顾,下有10多岁的孩子要养育。父亲为了给儿子治病,拿出自己一万多元的养老金。虽然第一次化疗效果还不错,可是没过多久,病情就开始恶化,化疗也不见效。最后换来的还是人走财空,白发人送黑发人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,章展接触越来越多的病患,经历越来越多的死亡。“刚开始,我觉得世界真的太不公平。但是慢慢的,我也想明白了,作为一名医生,我们自己必须要学会面对无法改变的病情,接受必定到来的死亡。我们把真实的病情告诉患者,对他们进行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和疏导,让他们去接受,利用有限的日子去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。无法改变的,我们只能接受。等到他们生命终结的那一刻,我告诉自己,他们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”章展告诉记者。
我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
“奖状?奖状和证书我都扔在家里的仓库里了。”当被问到中华骨髓库颁发给章展奖状的时候,他笑着摇摇头回答说。仓库,是摆放杂物的地方;仓库,是不被牵挂的角落。在章展的心中,捐献造血干细胞只不过是举手之劳,是不需要被记住的事情。“我觉得,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,不必要大肆宣扬。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,只是观念问题。我是一名医生,我知道捐献不会对自身产生什么不利影响;我是一名普通的青年,我应该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人重获新生。奖状、证书对我来说就是一张纸,病人可以拥有健康才是给我最好的礼物。”章展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。
“其实当初我来这个科室是被调剂的。”章展有些不好意思的告诉记者,“既然被选择了,那就不能逃避。”在大学的时候,章展接触最多的是临床上的内科、外科,血液肿瘤科是相当专业的科室。刚进血液肿瘤科的时候,他就跟着师父学习,“一切都得重新开始,如果不努力,就会跟不上节奏。”章展告诉记者,“其实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,你既然在这个岗位了,就必须要负责任。”
“如果病人的身体是一片田地,那那些肿瘤、病毒就是杂草,化疗就是农药,我们专科医生就是农药的撒播者。”章展这样比喻自己和自己的工作。
【作者】: 陈思祎 黄瑛蓓 【编辑】: 蒋梦莹